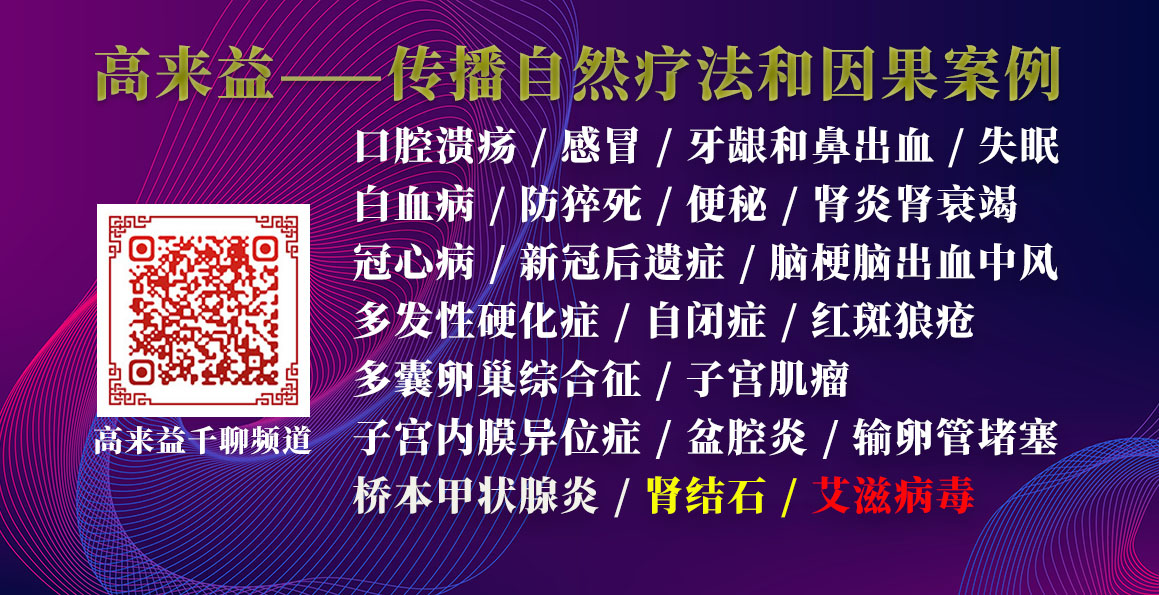来源:Brandi Velasquez(布兰迪·维拉斯奎兹,美国)

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性活跃——只有 13 岁。
我在情感上可能还不够成熟,无法进行性行为,但我有一个我信任的男朋友。
我们使用节育措施,但没有使用避孕套,因此我们无法预防性传播感染(STI)。
我不太担心通过性行为感染疾病——因为我相信我的男朋友只和我发生性关系,而且我每年接受性传播感染(包括艾滋病毒)检测。
13 岁时,我的艾滋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,14 岁和 15 岁时也是如此。
然而,在我 16 岁生日前 10 天,即 1996 年 11 月 7 日,我在进行HIV检测后接到了医生办公室的电话。

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,所以我独自坐公交车去了医生办公室。
我的医生告诉我——你确实是艾滋病毒阳性。
我感到崩溃和恐惧。
除了在电影《费城故事》中看到的内容之外,我对艾滋病毒和艾滋病了解不多。
医生说:“我很抱歉,在我的诊所里,我们无能为力”。
医生送我一些文件,让我填写,以便去一家专门治疗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健康诊所。
回到家,我把结果告诉了妈妈。除了她对我尖叫、羞辱我、责备我以及敲打前门之外,我不记得太多了。
我的男朋友也没有那么友善。当我告诉他时,他指责我作弊。
他很快就接受了检测,结果也呈艾滋病毒阳性。
此后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,但我们的关系并不健康,有时还存在虐待行为。

确诊几个月后,我开始服用大量药物来控制病情。这让我的胃感到非常恶心,直到今天,我一想到它就会感到恶心。
我没有很多朋友,家里也没有人可以寻求支持。但在我确诊后,生活变得更加孤独,我感到内心空虚。
在那之前的整个童年时期,在学校取得成功一直是我的首要任务。但一旦我被确诊,我的学术抱负就消失了,我所有的课程都不及格。为了残酷地提醒我的失败,母亲把我写满“F”的成绩单挂在墙上。
随着时间的流逝,我对照顾自己的投入越来越少。直到 2000 年我得知自己怀上了女儿,我才开始定期服用药物。
我希望女儿身体健康,也希望她在我体内保持健康。
令人惊讶的是,女儿丹妮拉出生时艾滋病毒呈阴性。
一旦我有了丹妮拉,我就再次停止服药。我不喜欢药物,而且我觉得没有意义,因为我已经不再怀孕了。

当丹妮拉还是个婴儿的时候,我遇见了杰森。
杰森是我哥哥的朋友,一开始我们并不合得来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们的感情越来越深厚。
那时,丹妮拉的父亲和我早已分居,杰森和我开始约会。
我与杰森发生了无保护性行为,但我没有告诉他我是艾滋病毒阳性。
我花了一些时间想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告诉他。我想我只是对男人太生气了——主要是因为过去被我的继父猥亵过——所以我当时并不在乎。
杰森最终通过别人发现我感染了艾滋病毒,他因为我没有亲自告诉他而感到不安,但他仍然想和我在一起。
我们进入了我一生中第一个真正相爱的关系。
随着我们关系的进展,杰森开始担心我没有按时服药,我向他保证我会为了他,为了丹妮拉而服药。
他看着我说:“不,你必须足够爱自己,要为你自己吃药。”
这是一个突破性的时刻。

爱自己对我来说从来都不重要。坦率地说,在遭受了一生的虐待之后,这很难做到。
我开始参加针对感染艾滋病毒的女性治疗和支持小组。
我学会了如何把自己放在第一位,并认识到如果不关心自己,我就无法真正关心别人。
杰森和我结婚了,我们在一起已经 21 年了。
我按照应该的方式服药,副作用并不像以前那么严重。
我还继续加深与女性艾滋病毒社区的关系,并为改善女性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生活付出了很多努力。
这些年来我遇到了很多出色的女性。不幸的是,许多人都已死于艾滋病,但她们对我生活的影响是永恒的。
今天丈夫问我:“你的最终目标是什么?”
他指的是我的宣传工作,该工作不仅关注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妇女,还关注艾滋病毒感染者的阴性家庭成员。
我回答杰森的问题:我的最终目标是留下一份遗产,让人们可以看到并说——她可能只是一个人,但她改变了世界。

点评
布兰迪是不幸的,也是幸运的,她感染后有女儿、丈夫和健康关系。
HIV感染者如果吃不了药物,还可以尝试自然方法,例如,高来益·艾滋病毒自然疗法,可以轻松控制病毒,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。
绝大多数的HIV感染者都源自乱搞,包括过早发生男女关系。
需要知道的是,没有结婚就发生男女关系也是犯邪淫。
邪淫是无数人生悲剧的罪魁祸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