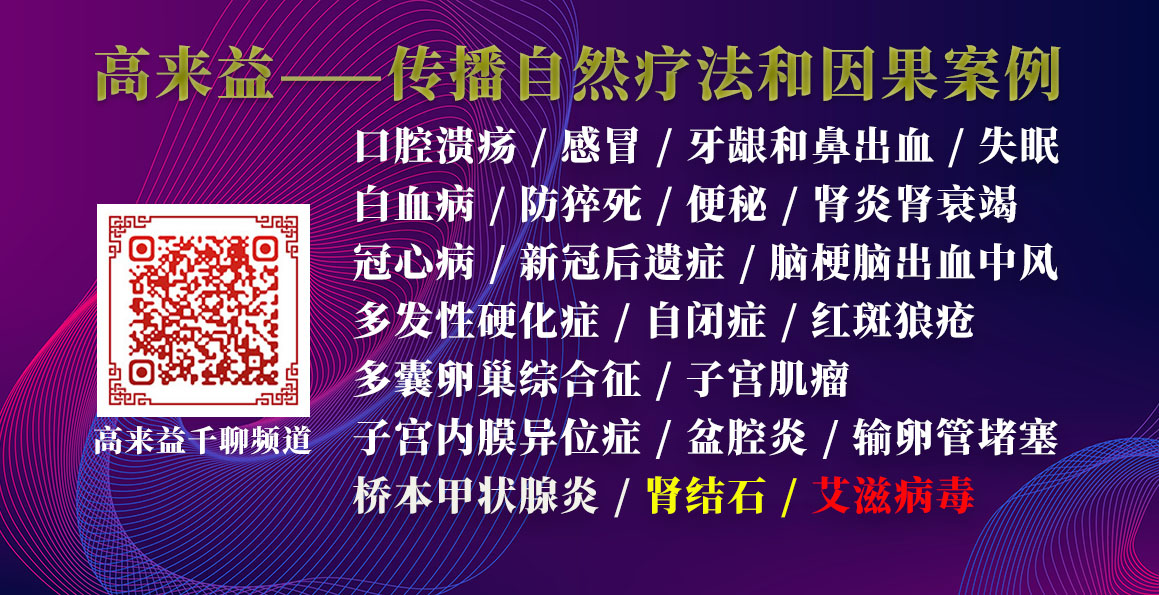安提戈涅·登普西(Antigone Dempsey)博士是一位艾滋病毒幸存者。1992 年左右,安提戈涅·登普西在关于年轻人和艾滋病毒的国会听证会上发表讲话(下图左一)。

登普西博士是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卫生资源和服务管理局(HRSA)艾滋病毒/艾滋病局政策和数据部主任。以下是登普西主任的自述。

我很感激能够生存下来,甚至蓬勃发展,拥有一个我从未想过的家庭和事业,而且,我对那些未能幸存的人深感悲痛。
作为一名年轻女性,我被诊断出感染了艾滋病毒,我亲眼目睹许多同龄人在 19 岁、20 岁、21 岁的时候就在我面前死去,她们(他们)没有机会成长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。
许多人去世时,家人从未接受过他们的艾滋病毒身份,因为他们要么是同性恋、双性恋、跨性别者,要么是不符合性别的人。直到今天,我的悲伤仍浮现在表面。
对我来说,工作就是将医学和科学进步的所有阶段与我生命的阶段结合起来。从 1990 年我 20 岁出头被诊断出艾滋病毒以来,一直到现在 50 多岁,我一直感染艾滋病毒。

艾滋病毒被写在我的身上——作为最早接受药物的人,我的身体仍然带有这些标记。有时我照镜子,感觉自己很坚强,但有时,我很痛苦。当我聆听老年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讲话时,我也听到了同样的感受。
作为艾滋病毒/艾滋病局政策和数据部主任,我有机会倾听我们服务对象的声音并制定应对策略。我听说过感染艾滋病毒的老龄化人群所面临的挑战,我们不仅仅关注抑制病毒的必要性——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同样重要。
在过去的 30 年里,我见证了许多演变和成长。对我来说,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科学发现,该发现表明,如果艾滋病毒受到抑制,就难以通过性行为将艾滋病毒传播给他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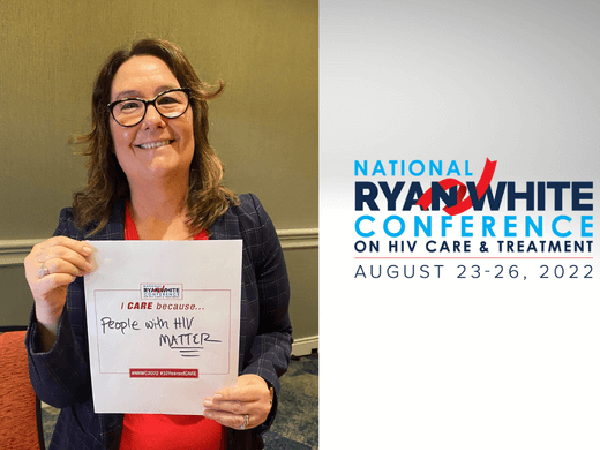
我清楚地记得 30多年前的那一刻,当我被告知艾滋病毒阳性时,我立刻感觉到墙壁在逼近,心想我要死了,没有人会再爱我,我永远不会有孩子。瞬间,我感受到了艾滋病毒的耻辱,泪水从脸上滚落——我的家人会因为握着我的手而退缩吗?
我成为了一个为艾滋病毒领域服务的工作者,我们这些艾滋病毒感染者在规划、开发、评估和提供服务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。事实上,许多首批服务项目都是由艾滋病毒感染者建立的。
我们现在正进入艾滋病毒的新阶段,希望通过将每年的传播人数减少到 3000 人以下来结束美国的艾滋病毒流行。我相信我们可以实现这一目标,但必须解决基于种族、性别、年龄和贫困的体制和系统性障碍。
对于我们这些艾滋病毒感染者来说,结束艾滋病毒流行也意味着承认我们经历的复杂性,并重视我们在过去 40年中为这一努力所做的贡献。它还意味着继续照顾那些幸存下来、茁壮成长并将继续生活很多年的人。

通过多年来分享我的故事,我希望这可以减少耻辱并帮助其他人讲述自己的故事。
当我遇到感染艾滋病毒的年轻人时,我可以告诉他们,我被诊断出的时候正是他们的年龄,而我现在就在这里——我在他们眼中看到了我的故事的影响,有时感到惊讶,但也充满希望。
我对此表示感谢,并感谢有机会领导政策制定、数据传播和创新,以确保艾滋病毒感染者能够获得优质护理和生活质量。
我这样做是为了那些没有幸存的人的名字。

登普西博士是幸运的,但许多人没有那么幸运。尽管当今的药物可以帮助感染者延长寿命或检测不到病毒的存在,但许许多多的人仍然在快速死去,因为不是每个感染者都有好的条件,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。
尽管绝大多数人感染艾滋病毒是因为邪淫,但罪不至死。他们依然有继续好好活着的权利。如果没有好的条件得到最好的药物和照顾,那么,自然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,例如高来益·艾滋病毒自然疗法。